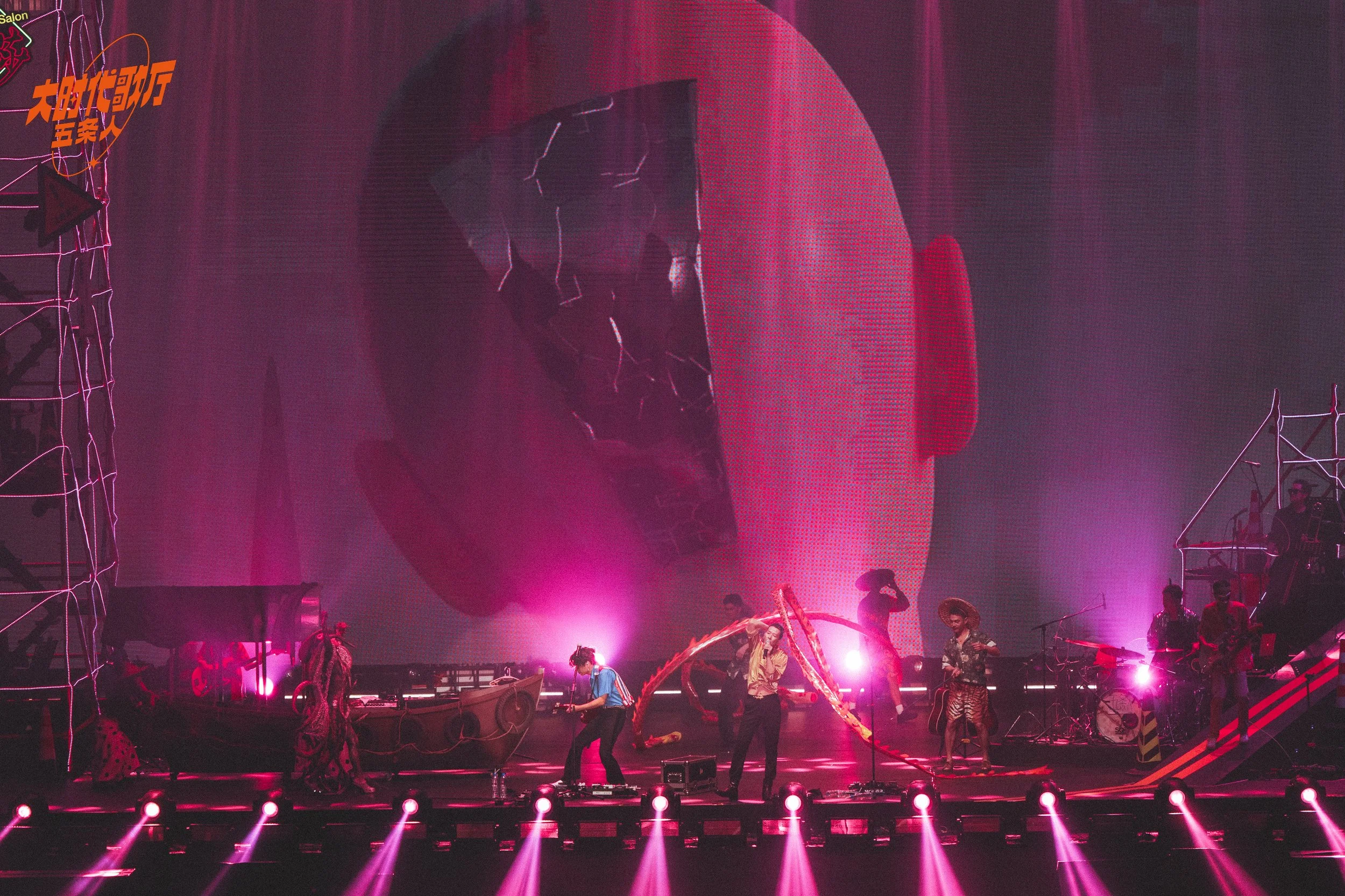帶著紅膠袋、踢著人字拖、唱著首首「戀曲
「曾揚言不羈的心只愛找開心
浪漫過一生 盡力笑得真
woo ho ho 我有我心底故事
霧裡看花一生走萬里 但已了解不變道理
無盡空虛 似把刀鋒靜靜穿過心窩 woo」
坊間對五條人的形容有很多,例如土產、民謠、迷幻、朋克、搖滾、野戲(一種非常臨時的狀態),如果要用一首歌去形容他們,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哥哥的《不羈的風》,那種浪漫不羈的浪子心,配上一口流利的方言,土味十足卻讓人無法自拔。訪問一開始討論的音樂風格已經直奔主題,音樂的一種生活性和其自身的無界限,他們隨意憑直覺聯想起的歌曲,已經可以拼貼出成為屬於他們的音樂特色。
五條人的音樂能如此吸引,相信正正不是我們日常所看到所謂學院派出身的音樂人能做到的,他們的作品是具有記錄性,充滿生命力的氛圍就恍如紀錄片,它們是具體、充滿生活的質感和趣味。
從你以為他們在東扯西扯中看五條人的音樂風格,就是不羈的風。
你們的音樂風格會讓我想起哥哥的《不羈的風》,好像無辦法完全觸摸得到,所以你們會怎樣形容自己呢?
茂濤 : 其實形容挺得好,完全初步觸摸到。
仁科 : 用beyond的一首歌,《農民》。
茂濤 : 《不再猶豫》。
仁科 : 《無盡空虛》。
茂濤 : 其實形容得對,編輯就用這個吧。
仁科 : 畢竟第一次在香港演出賣了4張票,所以我們對香港這個市場很謙虛。來香港就很多次,我覺得不下20次吧。還記得第一次賣了4張票,2張是外國人,結束之後我們和一起來的一個叫阿東去吃宵夜,他就是給一名著名的導演拍紀錄片的,他還邀請了那兩個外國人。上電梯的時候我提醒了他一下,「我們才賣了幾張票,這個宵夜好貴。」,最後還是請別人出費的。所以這次是1000多人的場吧,能賣掉也是個奇蹟。
( 但聽上去他們完全不介意是不是個奇蹟!)
就你們個人而言,有特別偏好和喜愛的音樂風格嗎?例如有什麼作品讓你們喜歡上音樂繼而有創作的慾望?
仁科 : 我最近聽情歌比較多,最多的是 Georges Delerue 的一個電影配樂,《 The Woman Next Door 》中一首6、7分鐘的歌。
茂濤 : 我聽得很雜,情歌肯定經常聽啊,還有最近自由爵士聽得比較多,因為最近不是去美國巡演嘛,買了很多唱片,買自由爵士比較多,還有一個很很喜歡的樂團,叫芝加哥藝術團 Art Ensemble Of Chicago。
請告訴全世界,海豐話永遠就是一種「回歸」!
相信用家鄉語言海豐話作為創作元素之一是你們的一個標誌性特點,所以你們的作品經常性讓我聯想到一些喜歡用台語創作的台灣獨立樂隊,有趣的是這涉及到一種語言的歸類,台語和海豐話都是閩南語系分支出來的語言。最開始選擇以這種模式創作時有沒有一些現實的考量?例如不被理解、沒有人聽得明白、傳播性不夠廣闊?
茂濤 : 完全沒有,我們那個時候想用海豐話創作,純屬就是就想做音樂,而且一種新的一種嘗試嘛。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是聽了台灣的一些樂隊,他們亦用方言演唱,還有林生祥(台灣高雄的獨立音樂創作人,擅長創作關懷鄉土的客語音樂。)。
當時我覺得他們把音樂和語言融合起來這件事特別有意思,就是非常有生活感。就好像平時在吵架時,你會感受到中間的語言,所以就想嘗試用海豐話跟音樂結合,結果就一發不可收拾。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每一個地方的語言都有它的獨特性,其實就是它的一個性格,就比如像閩南語,它也有一些的地方性、潮州話它相對是軟一點的。而我們那邊的音調是比較硬的,所以碰撞出來呢亦符合我們自己,感覺就是有性格的音樂。現在也有很多人嘗試用方言來演唱,但我總覺得很多時候他們沒有捉住語言本身的特性:就是一種有性格的東西。
仁科 : 其實用海豐話創作在當時來說它是一種「回歸」,雖然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出發」,因為那個時候中國搖滾大多數是普通話,我們自己也有刻意練習普通話,但你會發現不論用普通話或是英文,我覺得這一種用不熟悉的語言去到達另一種東西是一種「出發」,但海豐話對我們來說永遠就是一種「回歸」。
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
非常記得《縣城記》封面寫着,「立足世界,放眼海豐」,你們似乎把海豐作為生命的中心,其餘的地方和文化則已經是「世界」,有一句來自哲學家的說話經常聽到,「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 維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 ,所以我認為語言是你們的音樂藝術裏非常值得探討的一個核心,不單止是用方言創作,更是牽涉到創作的自由度和語言的邊界,所以音樂對你們而言它最大的自由是否就是不受言語的限制和約束?
仁科 : 沒錯,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就好比有很多人,他去到美國生活了一年,他都沒有進入到西方的世界,因為他沒有進入那種語言。語言承載了很多東西,例如文化,所以人不光是消費這個文化,只有使用那種語言,你才能進入到那個世界。哪怕我現在在這裡,我不跟任何人交流,但我會法文,那我已經進入了法國的世界。
音樂就是世界的語言,記得以前擺地攤買唱片旁邊有一個小販,他的那個紙皮箱上面的招牌寫着「音樂無國度」,拋開語言這種文字的符號性,它就是沒有一個界限。
茂濤 : 對的,在小程度來說語言就是一種溝通,就像所有人都可以通過音樂載歌載舞,像仁科剛才說的,其實就是一個語言環境的問題。
仁科 : 我舉個例子,我們都很喜歡聽馬里音樂,他們用的是班巴拉語,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唱什麼,只聽到有一句說話很像是「一條魚」。然後我就瞎唱,唱着唱着就是《地球儀》這首歌,裏面的「馬里共和國 我釣到一條魚」靈感就是來自這裏。所以按上述我所說的,我當然進不了馬里和這個語言系統,因為根本不懂。但是大家通過音樂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片風景,而透過這首歌所看到馬里風景是靠我的想像,我試圖進入一個只有我自己能理解的馬里。
當語言發展成為音樂的時候,並不是用作溝通。
會否考慮到想表達的訊息不能完整傳遞給聽眾?畢竟現在的創作的確多了普通話和英文,是有考量到這一點嗎?
仁科 : 回到維特根斯坦他的內心理論吧,有些時候語言也是遊戲有文字遊戲。就對我們來說,歌曲創作,比如在《 Canton Express》這首歌裡面出現了粵語跟普通話,它對我們來說是很好玩的一種遊戲。甚至是在耶魯演講(在美國巡演的時候,五條人還去到了耶魯大學進行交流,談及到鄉城文化差別、全球化、本土主義等等的話題。)的時候那個教授說這首歌缺乏某種深度,事實上這首歌根本沒有任何深度。而這首歌其實就像剪紙,就好像剪了各種快速的新聞報道,然後拼貼成一種歌詞,對我們來說他就好像一份繪畫作品。
茂濤 : 它就是一種生活狀態嘛。
仁科 : 語言本來不是用溝通,它是內化一種情緒,就算用音樂溝通,我覺得更多的是一種感受。就好像我們看藝術作品,你也不會聯想到要和畫家產生任何溝通,所以為什麼會想通過一首歌去產生溝通?就算是詩,詩人更多的在寫自己的一種內化問題。語言可以是一種日常溝通,但發展到音樂的時候,它並不是我們用作溝通。
創作不是一種策略,是一種養生,它拼貼出來的東西具有記錄性。
過去的專輯基本上都是寫一些個民間、城鄉文化、社會性事情為主,近年則偏向個人閲讀、思考面向、對世界的一些期願。感覺你們由外在環境變成向內化的創作,所以音樂似乎已經演變成你們表達思維的媒介?
仁科 : 其實沒有,去年出的那個新專輯裡面的故事是很具體。當然它肯定是包含情緒的,還有一種就是寫歌也是像一種養生的,寫一首歌你自己很舒服很開心。也是一種遊戲。 裏面亦可以包含一些密碼可能是學園酒後突然間發揮了一些歌詞是對某人或某一種狀態說的。另外一種就是有很多東西你再寫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例如《夜已晚》的創作是寫在一張紙上面,但事實上當時我寫了什麼我現在也忘記了,但當時怎樣形成亦不是最重要。
茂濤 : 是的,所以在創作的時候很多時的情緒、喜怒哀樂、對一些東西的思念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反而就是通過音樂抓着和表現那種情緒。就好像以前有一首《鮮花在岸上開》,其實它就是一首很簡單的情歌。另外就是一些很現實的狀況,把那些我們所看到的用音樂把它呈現出來,例如《豬肉炒辣椒》,它就是記錄了一個在疫情期間發生的一件事。所以創作都是建基於一些所見所聞,和當刻想寫出來的東西。
最近有沒有一些新的題材類型或未來方向想要嘗試?
仁科 : 我的創作就是記錄,我是學卡維諾 ( 義大利作家,主要寫奇特和充滿想像的寓言作品。 ),把很多東西記錄下來作備用,需要的時候就把它們變成歌。就好像一個烹飪過程把一些食材炒好,繼而再把它們分類。而我亦提到最近聽比較多的是情歌,所以接下來的一些新方向可能也跟這方面有關係。
茂濤 : 隨心所欲類,不設限。
仁科 : 現在主要根據自己的感受先走一段,因為它不是一種策略,是一種養生,不一定是每天醒來就是有一個思維動向。
拍電影這個心,從來沒有死亡過。
有趣的是你們的作品雖然非常「貼地」,卻經常性為它們想像一些故事背景,是因為你們本來是電影愛好者的原故嗎?例如《故事會》,它是寫過一些劇本,本來是要拍電影的吧?
仁科 : 拍電影這個心從來沒有死亡過,就是一直想想做。但是停留在思維,因為這個事情當時拍的預告片就知道它的複雜程度。《故事會》的時候我是有這麼一個想法,因為它很多歌曲,當時以《爛尾樓》為開始,然後很多歌確實慢慢寫著寫著它們可以串起來。而《爛尾樓》是去惠州演出的時候,當時那個 live house 的老闆告訴我們,在這個城市的中間有一棟爛尾樓,但它在鬧市裡面住了很多年啦。然後我們經過的時候看了,然後就產生了很多對電影的想像。
然後包括到了後面用 25 個小時來拍一個預告片的《南方戀曲》,是想做一張沒有電影的的電影原聲,但它後來什麼都有了,影片有了,讓人寫的影評,還做了海報,還有各種劇照。
茂濤 : 我把那預告片放給那個演我表妹的董晴,她喜歡得不得了。
仁科 : 這是我作為導演的第一部預告。當時其實有很多人還是想拍電影,但那時候因為我們有個經紀人叫張老周,他就把很多電影的東西他自己給推掉,可能他有他們的考慮,後來隔了兩年後才知道這些事。不過當時的確很忙,雖然後來很多人會拿這個影片來說,因為它真的是拍得好看,我記得當時還是要求了用專業團隊 25 個小時就用了 10 萬多,而預告片的執行導演就是入圍了柏林電影節的《白塔之光》的導演。當時很有激情做這個事情,後來歲月慢慢的消磨了一點東西,但是那個激情可能會變成另外一種東西。
所以電影和音樂在你們的作品中有沒有互相影響彼此?
仁科 : 對我來說,從一開始就就是有影響,一開始就跟電影愛好者,而電影裡面有很多好聽的音樂。我們說電影配樂,例如 Quentin Jerome Tarantino 的電影裏面可以聽到各類型很豐富的音樂,一套電影裏面已經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音樂。好像上次我們在電影節看的《Disco Boy》,它裏面有很多很cool的音樂,所以電影對我創作的音樂有很深的影響。
茂濤 : 對只要電影裏面的配樂一響起,那種畫面就會自然出來,例如《德州巴黎 Paris, Texas 》,裏面的結他聲一響起那種荒涼感;又例如《天堂電影院 Nuovo Cinema Paradiso》那個音樂一起來就貫穿了整個畫面和旋律,我覺得這兩者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這個城市無法被取替的東西,就是五條人和香港之間的回憶。
來了香港開演唱會這麼多次,就你們而言,這個城市有什麼特別、無法被取替的東西?
茂濤 : 我現在立馬能想到的一個記憶點,最深刻的是我們有一個朋友,每逢我們去香港演出的時候他都會去接我們,然後去7-11 買啤酒請我們喝,然後我們會在街頭一邊喝啤酒一邊閑聊一邊走,我覺得特別舒服。我覺得就是這個回憶讓我特別想到香港的街頭和生活感。
仁科 : 我覺得香港就像剛才我們所聊的電影,它也是一個電影城市,例如他們的廟街、重慶大廈總會找到那些電影的印記,這些是它無法被取替的歷史。 就好像剛剛阿茂提到的那個朋友,我還記得當時我們一邊喝酒一邊逛街,碰到很多流浪藝人、還有一些陰陽人打扮,所以香港給我的印象是很輕鬆的。
茂濤 : 另外香港還是一個流行音樂的城市,就好像我們的《南方戀曲》也是跟香港有關係的。
有什麼香港音樂曾經影響你們的創作?以前的訪問好像提過張學友。
茂濤 : 我跟你講,後其實以前老是說都是四大天王那些,但是李克勤,我覺得這個人其實也很厲害,我最近在聽他幾首歌,真的太好聽了,有一首叫《癡情伴侶》,還有《護花使者》